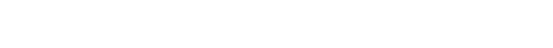关敬如
在太阳集团官网建校115周年和西迁乐山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令我醒目的是,1944年考进太阳集团官网经济系老前辈田林先生的《回忆峨眉居社》文章,文中提及曾启贤先生,他这样写道“我们对面一排朝阳的房子,住的是经济系研究生,有朱馨远,万典武,曾启贤等。唯一常到宿舍来的女生是丁茔,因她个子小,年纪轻,小巧玲珑,我们都爱喊她小丁茔,是曾启贤的女朋友,后来喜结连理。”……这一段记载,不犹唤起我对导师的追忆。
曾启贤老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今年的2月9日是他仙逝二十周年纪念日。1989年2月正值中国农历春节期间,时任太阳集团官网经济学院院长的汤在新教授打来电话,告知曾启贤老师病逝了……,这一消息对我来讲既难以接受也难以置信,可以说是晴天霹雳,因为刚刚在北京机场迎送曾老师去欧洲学术访问,又刚刚为自己赴英留学访问之事征询导师的意见……,一切都发生的这样突然。在田源师兄和我[i]赶往武汉参加追悼会之前,与我以后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董辅礽先生通了电话,他称由于公务在身不能前往,特意嘱托我也代表他为曾启贤老师送行,董老师在电话里对曾启贤先生所给予的评价,尽管细节我不能清晰地去复述,但主要意思我依然梗概的记得,曾启贤老师是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学术研究领域之宽泛、之深邃,治学之严谨、之勤奋,对经济学各个学派、流派之娴熟,对东、西方经济学乃至东欧经济学演变和现状之了解,达到了融会贯通、驾轻就熟的程度,他不拘泥于传统和教条,是经济学界思想活跃、锐意进取和勇于创新的代表人物……
曾启贤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严肃而又具师道的导师、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是风度翩翩的教授;他惜才、爱才,更塑造人才,他对年轻的大学生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同系别、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学生,特别是进入自主学习和研究时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相当多的学生研究生同他有着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接触和联系,都视他为导师,有问题向他请教、向他探讨;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毋庸置疑他是青年学生的一面学术旗帜和思想核心,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武汉,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只要有曾启贤老师的出现就会有各种聚会和研讨,他涉猎宽泛的知识涵量、他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他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他率真秉直的性格品行都成为学术集会、研讨会的聚众亮点。曾启贤先生和时任院长和副院长的汤在新教授、伍新木教授等师生一道创造了经济学院空前的自由学术氛围和创新思维空间。
曾启贤老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二十年前的1989年去世时仅68岁,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夺去了他妻子的生命,逼疯了他唯一的儿子,他鳏寡孤独地生活似乎积聚了巨大的学术能量,焕发了迟来的学术青春。1980年,他作为主要编写者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室主持编写的《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这是一部体现“发展是硬道理”思想的政策指引性书籍,尔后他又承担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历史的考察》和《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两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实践的理论探讨。曾启贤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本科毕业后,师从张培刚教授,是张教授的第一批研究生和得意高足。他从张培刚教授那里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训练,熟读过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跟踪西方经济学在当代的演变和发展,为此他既熟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又具有深厚的西方经济学功底,这对他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较早关注经济学中的稀缺性原理、对“人”的分析,宏观与微观分析、实证与规范方法、静态与动态分析、均衡与非均衡分析等等。他还活跃于国内国际学术舞台,先后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去美国、法国、联邦德国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为会议提交论文,发表意见,从而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波兰社会主义改革的经济学家弗·布鲁斯(Virlyn W Bruse),捷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 (Ota Sik) ,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纳(Kornal, J.)都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在出版业并不繁荣的当年,曾启贤先生撰有论文《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试评》,主编《按劳分配有关范畴的分析》,共同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其部分重要论文收录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分析》。
曾启贤先生把生命最后几年的光阴献给了国家的改革事业,献给了学术研究和他培养的学生。他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框架、体系与机理的最早探拓者之一,也是中国企业走股份制道路的最早倡导者之一[ii]。他培养的学生要求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北欧社会制度模式,要求懂数学、计量等实证分析的方法,注重基础资料和数据的收集、积累和运用。他给学生所传授、所给予是经济学基础、是逻辑和辩证的方法、是比较和不拘泥于传统的创新思维。
在鲜花丛里、哀乐声中,追悼会和遗体告别的场面始终在我的清晰记忆中,我一直伴随在老师的身旁,这是最后一眼、这是最后一次接触、这是最后一次聆听,不舍的我推着灵车直至殡仪馆的炼炉……, 实在不愿回忆,因为这太令人伤感;然而又常常不能忘怀,因为是那样的刻骨铭心。
在这里祭奠导师也有另外的一份寄托,那是2005年秋季出差深圳,顺道去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探望曾启贤先生的挚友汤在新教授。我们在一起谈到曾先生,缅怀之情溢于言表,他同我商量在曾先生二十周年忌日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然而今天我不得不同时痛哭在两年前去世的、让我一生都不能忘怀恩师汤在新教授[iii],我也以此文践行汤老师嘱托。